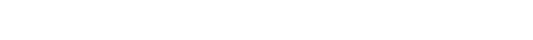-
小案件大作为!李一冰律师团队成功办理小额装修纠纷案
在法律服务领域,大额案件往往备受瞩目,但小额案件同样关乎普通人的切身利益。近日,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李一冰团队成功办理了一起小额装修合同纠纷案,不仅成功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还彰显了明炬律师在小额法律服务领域的专业价值与社会责任。
more -
白强、王黎:《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修订亮点解读
2025年1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新的《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适用《规定》。
more -
数字资产在迪拜:政策与现状
据Statista数据,2023年,沙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占总GDP的50%,在阿联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贡献了27%的GDP。2024年10月,由于地缘冲突持续以及OPEC+石油减产协议长期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4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2.1%的低迷水平,与4月份的预测相比,GDP增长预期下调了0.6个百分点。面对石油资源市场的危机,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区块链和加密产业,让阿联酋、沙特、萨尔瓦多等在内的一些小国看到了新的生机。
more -
新《公司法》下的企业反舞弊合规与调查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过程中,舞弊现象愈发猖獗。财务造假、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舞弊行为屡见不鲜,这给企业自身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与发展。
more -
律师受香港公司委托在内地起诉案件实务要点
随着中国内地的经济腾飞繁荣,越来越多港资、外资企业与内地进行交易合作,香港公司在内地的诉讼业务也日渐增加。律师在接受香港公司委托诉讼业务时,需要特别注意程序上的特殊要求。
more -
大S的离世:再谈遗产继承一二事
近日,台湾著名艺人徐熙媛(艺名大S)突然离世,这一噩耗震惊了许多人,大S作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她的离世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而作为一名法律人,在缅怀逝者、感叹青春的同时,更需以理性目光审视生命终结后的法律命题——当个体生命画上休止符,其遗留的财产将遵循何种路径完成代际传承。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