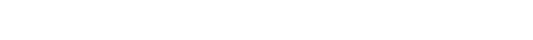-
律师事务所成立共青团组织的功能性与必要性 ——基于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团建工作展开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作为中国西部律师界的“航母”律所之一,始终将共青团建设视为推动事务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明炬党委的坚强领导与指导下,共青团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支部委员会于2022年8月10日成立,并于2024年4月7日升格为共青团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委员会(以下简称“明炬团委”)。明炬团委始终坚持“团建促所建”的关键任务,紧密围绕青年律师的发展、专业技能的增强和社会责任的履行等关键方面,精心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团建架构。以及通过构建组织、引导思想、创新活动等多元化方法,为青年律师提供了广阔的成长平台,为事务所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more -
李杰:新《公司法》下董事的催缴出资义务研究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负有催缴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股东出资的义务,该条款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对于董事是否应当承担催缴义务以及未催缴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争议。但是,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仍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即董事催缴义务在何时应当履行?如何认定董事是否未履行催缴义务?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应承担何等责任等。因此,本文将以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为基础,探寻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理论基础、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认定与行使、厘清董事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时的责任认定与合理限制,为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适用提供一定解决思路。
more -
华雨:减轻型坦白——认定及其辩护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坦白制度,首次将“坦白从宽”予以法定化。尔后十余年,坦白从宽及其量刑从轻直接被海量地体现在裁判实践之中。然而,“坦白只可从轻”几乎已成为思维定式;“坦白”与“减轻处罚”不发生关联也好似成为约定俗成之“共识”。
more -
王黎:企业应对行政处罚的8条实务建议
近年来,执法部门加强了食品药品、医疗、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广告营销等领域的执法力度,与企业有关的行政处罚案件日益增多。企业一旦遭受行政处罚,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商业风险。
more -
杨砚律师团队:承包人视角下利润索赔实务指南
在工程实践中,索赔通常依据其目的和要求被划分为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这里的费用索赔是指承包人寻求的经济补偿,包含施工成本损失以及利润损失,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规范中,费用和利润是两个明确区分的概念。费用通常指的是完成工程所需的成本,而利润则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后获得的盈利。本文将利润损失赔偿,这一通常包含在费用索赔中的部分,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利润索赔这一概念。
more -
为之商事诉讼团队:申请再审的期限是多久?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原则上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