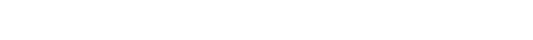-
邱永兰:典型案例视阈下“不宜强制履行之债”的认定规则与司法处理逻辑
“不宜强制履行之债”的认定与处理,是《民法典》违约责任制度与司法实践交互的典型场域。本文引入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以合同自由原则为逻辑起点,结合合同僵局化解的现实需求与司法权的功能边界,系统梳理司法实践中“不宜强制履行”的认定规则与方法论逻辑。
more -
民专委罗丹:未成年人校园人身损害纠纷的责任界定
校园人身损害纠纷主要涉及查明事实、划分责任比例及确定赔偿金额。准确在纠纷中界定各方责任,不仅有利于保障受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本文将围绕未成年人校园人身损害纠纷的责任界定展开探讨。
more -
陈霞律师:“捐赠型受贿”及“代为保管型受贿”的认定
张某被指控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利用担任某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李某、王某等人在医疗设备及耗材供应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李某、王某等人现金50万元,并以“捐款”“捐物”为名,“收受”李某、王某等人所送财物共计256万元。受捐赠单位(学校、医院)与捐款人有的签订了书面的捐赠协议,有的虽未签订捐赠协议但颁发了捐赠证明,这些款物全部是受捐赠单位真实收取,也是真实用于受捐赠单位,受捐赠单位并不是张某的特定关系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所谓的“犯意联络”,受捐赠单位没有帮助受贿的故意,且本案所有捐赠都是公益捐赠。
more -
邱成捷、梁开阔:浅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八十条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向社会公众公示。笔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八十条,从细化期限标准、明确后果边界、规范纠错程序设计提出自己的思考。
more -
王黎、白强:律师协助办理政府采购投诉案件实务分析
政府采购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财政部门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供应商如认为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权益受到损害,可通过质疑、投诉等途径寻求救济。
more -
王芬:外国离婚判决在我国国内如何申请承认与执行
随着国际间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婚姻数量不断增多,随之产生的离婚纠纷也日益显现。对于已取得外国离婚判决的当事人,若需在中国境内办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事宜,应注意: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不能自动在中国境内发生法律效力,必须通过中国法院的承认程序。 本文将从实务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外国离婚判决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流程、法律依据及注意事项,为有相关需求的当事人提供指引。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