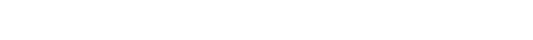-
为之商事诉讼团队:剥夺当事人辩论权与其他再审事由的关联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的十三项再审事由,从文义上理解,似乎均为各自独立的再审事由,但经深入研究即可发现,在特定情形下,“剥夺辩论权利”也与其他再审事由存在一定关联。
more -
范自力团队:追加公司股东的锦囊妙计
在与公司的交易中,交易者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公司无力偿债,而股东却逍遥法外。许多交易者即便手握生效裁判,但也常常因为公司资产空虚、股东有限责任而陷入困境。今天,笔者将为各位提供追加公司股东的方法,以保障交易者债权的实现!
more -
知识产权专委会:法院判了!网店提供游戏道具“代充”服务构成不正当竞争
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是热门手机游戏《动物餐厅》的开发和运营商。该游戏自上线以来,凭借独特的玩法和精美的设计,在微博、豆瓣、知乎、B站等平台积累了大量的玩家群体和良好口碑。游戏中的虚拟道具如“鱼干”“盘子”“鱼饵”等,玩家可通过官方充值渠道购买,这是原告的重要收入来源。
more -
从检察院一民事抗诉案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第三者的财产返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第三者财产行为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应当全部返还是部分返还?以上问题是这类案件的常见争议。在冯某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核心争议在于该赠与行为是否无效?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离婚时是否能够直接认定为各占50%?可否仅返还50%?让我们一起从本案中探寻答案,为类似纠纷的妥善处理提供实践指引。
more -
杨天武、张怡然:民营经济迎来投融资东风
《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于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纵观整部法律,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有众多利好,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必将呈现新气象。笔者尤其关注民营经济在投资融资方面的新规,本文就此做简要解读,以期民营经济乘势而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more -
叶浩:新公司法——董监高的责任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以下称新公司法)已于2024年7月1日施行,此次新公司法大修,调整的地方不少,其中改变最大部分之一就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的精细化。本文就新公司法下,董监高责任变化展开讨论。
more
© 2023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蜀ICP备19018548号
技术支持:创企科技